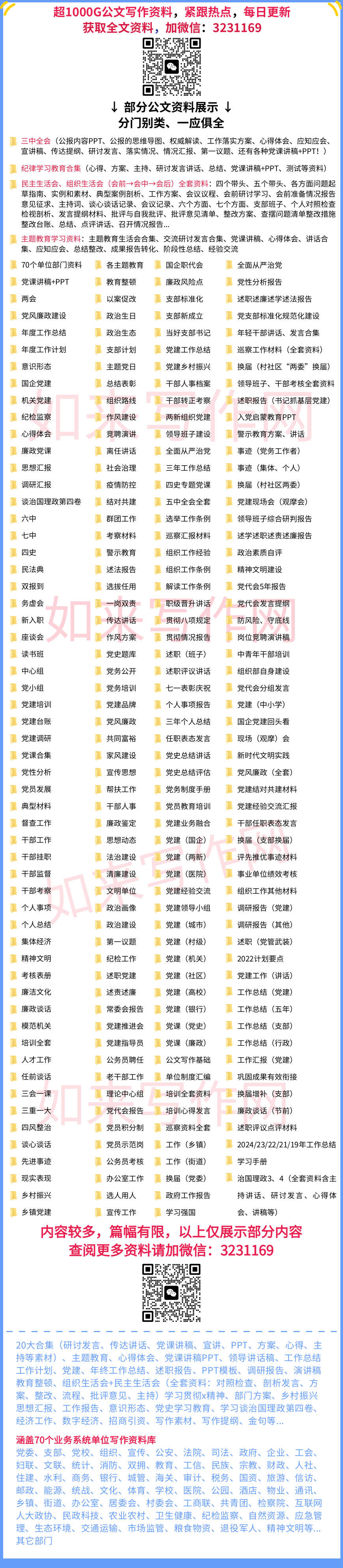楼是座老楼,斑驳的外墙与霉迹里,可以品读出20世纪末的风情。焦热的光线从挂满锈迹的窗口进入楼道,玻璃将它筛成颇具神秘感的钴蓝色。桂芬同隔壁单元的太太打完招呼,挥了挥手,笑了一下。笑容藏在蓝色口罩下,并未被察觉。
踏入楼道时,从极热的外边进入阴凉,温度的变化让她有些恍惚。家在二楼,可在通向二楼的平台上,她就不得不歇一会儿了。桂芬把拎着的袋子放在地上,微微屈膝,揉一揉半月板的位置。“可能是真的老了吧。前年做完手术那会儿还没这么疼,现在就连笑一下,都能感觉到眼角皱纹正在不断深刻。”这样想时,口罩让呼吸变得不畅,但还没到家,不能随便摘了。桂芬揉了揉鼻子,揩去从鬓角流下的汗,准备继续走。
桂芬要回家给老李做长寿面。老头过生日,不稀罕蛋糕之类的西洋吃食,画着寿桃写着寿字的奶油蛋糕不过是走个形式,最后也是被年轻人分了。唯有一碗面条最得老李心意。
桂芬爬上二楼,找出钥匙捅开门锁。窗子紧扣着。昏暗,狭小的空间,容纳着两个人半辈子的时光线索。线香的话梅味,与房间里陈旧的气息矛盾。窗子一开,陈乏感便一涌而出,漫无边际的夏向四面八方,以阳光与热浪的方式奔袭。刚才外边还稍有喧嚣,顷刻间便很有默契地消失了。代替人声的,是虫鸣和鸟啼,它们替人们控诉着夏末的最后一点儿炎热。
社区通知,疫情逐渐向好,可以出门活动一小时。哪有一个夏天像今年这么安静呢?她看了一会儿外面的世界,这个地方的夏天,被抹去了许多生气,用来代替的,是紧张与不安。路上,只有穿蓝色防护服、戴防护面罩的志愿者走动,他们不时会接到命令,紧急集合,奔赴所需位置。恍惚感有些加重了:老李,现在也在这蓝色的人群里吧。
桂芬扎进软绵绵的床垫,闭上眼睛。窗外微风拂动,撩起窗帘又轻轻放下。她躺在原本老李的位置,鼻子轻轻追寻着他的气味。嗅了一会儿,她突然笑了,“都这个年纪了,还整这些干什么。”桂芬把老李身上的味道总结为专属老男人的臭味,嘲笑他退休没多久就溢出老人臭了,老李红着脸辩解,这是因为自己闲的。
那是一种什么味道呢?是年轻时从事劳动起积攒下的汗水,是几十年烟龄累积下的淡淡烟草,是退休后在厨房里整日捣鼓染上的油烟……每一种气味在过去,都是桂芬想用更多的洗衣液与柔顺剂掩盖的,此刻,却幻化成一种缱绻于心头的馥郁,生怕一丁点儿被时光掳走。
桂芬悄悄翻身,好像生怕打扰到睡在床上的另一个人。她环顾四周,每一处都有熟悉的影子,角落的书桌上,摆着老李的书,大多是20世纪出版的。这些书曾经都有过鲜艳的封皮,但翻阅久了,颜色变得暗淡,书名的油墨也糊成一团。老李喜欢在这抽烟,一边取一本书读。自那场大病后,他刻意减少了吸烟的量,开始喝茶。看书的习惯没变,很多时候老李会捧起一杯香茗,另一手端书,带着花镜在屋里游荡,弄得满屋子茶香四溢。
这些细节足够她回忆一辈子,一直陪她到再难以用语言表达意思的那天。即将坠入睡梦的那一刻,手机响了。女婿才给她和老李换的智能手机,还不太会用。桂芬想就这么睡吧,不管它了。可铃声越来越大,没有挂断的意思。几经思想斗争,她还是把手机掏了出来,是女儿打的。她按照老李教的,把屏幕上的滑块滑一下,女儿的声音就出现在听筒的另一侧:
“妈,听说了吗,估计还有几天就解封了。”
“听说了,今天我们这儿还让下楼买个菜,你们那边呢?”
“一样的,我和小乔刚也下去走了走,买了些吃的……”
“你怀着孕呢,怎么好下楼乱走?现在又不是完全好了,外面可能……”
“没事的妈,我戴着口罩呢,小乔把我照顾得挺好,他做饭呢。等解封了,再去商量我爸的事吧。”
电话挂断的那刻,幽幽的,房间再次沦入寂静。桂芬倚倒在床头,思考着,以后该怎么给外孙说他姥爷呢?在他央求要听个姥爷的故事时,把他搂进怀里,告诉他姥爷是个英雄?还是个普通人?睡意一点点地被驱散。桂芬想,她得尽快适应这种步入老年后,不知什么时候就陷入疲倦的感觉。
床头柜上放着老李未来得及穿的一套防护服,戴过的志愿者袖标,还有一个党徽,摆在中央,日光照耀下,投射出温暖的光芒。桂芬把徽章捧进手心里,感受它的温度。
“镰刀”与“铁锤”,“为人民服务”,这些,让桂芬渐渐陷入痴醉,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干劲的、属于她的青春年代,看到老李双腿陷入脏兮兮的泥浆,挺起上身落锤打桩;又看见老李蹲在车间里,一边又一遍对照图纸,拧紧螺丝,焊接最后一根辐条……他总是干得很多,却比任何人都快乐。他曾被打桩锤的木杆震得一手血泡,原本写字的手结满了死皮和老茧;他曾被机床上的快锯割伤,洒了一地血,也只是包扎休息了片刻又回到岗位。直到某天午饭,一瓶难得的橘子汽水被递到自己手里,眼里满是老李憨厚的笑:“你能嫁给我吗?”桂芬就知道,自己终究要嫁给一个夏天出生的人。
桂芬始终觉得自己有一种摆脱不了的、属于少女的情愫,那就是觉得自己嫁对了人。这个男人好脾气,不偏执,不执拗,却对自己相信的无比忠诚。他希望别人好;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;他总是出于真心。1997年洪灾,他打报告申请救灾,被告知不用,有我们人民子弟兵呢;2008年汶川地震,他交材料申请去支援,被告知不用,有我们人民子弟兵呢,况且震区不稳定,别来添乱……命运一次又一次把这个男人从无法预言的天灾边缘拉回到自己身旁,给予她最丰厚的幸运。然而谁都想不到,疫情在这个夏天,会再一次侵袭这座离海最远的城市……
记忆里,那些过去的,比现在热上几倍的夏天刮起了飒飒的风。这是坠入历史,即将被遗忘的前兆吗?不会……不会的,桂芬想在有生之年里把这些都记下,甚至在它完全失去色彩前用笔写下,写成一本册子留给外孙,叫他长大后慢慢看,慢慢读,不仅要让他知道在他出生那年发生了什么,让他知道素未谋面的姥爷是怎样的,还要让他看看属于那个时代的罗曼蒂克。
“喂小孩儿,回去!快回去!把口罩给我戴好,把鼻子捂住。你也七八岁了吧还不懂事?怎么跑出来了,你家大人呢?”一连串的发问,略带严厉,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年轻的志愿者。
“叔叔你就等我一会儿,我办个事。”童声显得沉闷,应该是口罩的缘故。
“你一小娃娃有啥事可办的?快给我回家!你家在哪呀,我送你……嘿,你别跑呀!站住……”
桂芬走到窗边。二楼,楼下的情形挺清楚,一个男孩子,七八岁,站在阳光里,口罩捂着大半张脸,直勾勾盯着她家窗口。清澈的眸子犹如两口泉眼,澄澈的无邪都快溢出来了。志愿者站在一旁,看小家伙能耍出什么花样。桂芬觉得奇怪,目光藏在窗帘后边。这么对视一会儿,男孩从背在身后的手里捏出一个东西,向前一步,轻轻放在路基石上,又找来一块小石头压住,肃穆地站了片刻。身旁的志愿者看到这一幕,声音柔软下来,蹲下在孩子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,然后去牵男孩的手,向隔壁单元走了。
桂芬取来眼镜向楼下看,路基石上的,是朵蒲公英,挺大的一颗,小小的石子压着它柔软的茎,防止被吹跑了。花团还挺大。这孩子从哪整来这么大的蒲公英啊?一阵热浪来袭,蒲公英散了,细微的花绒飞向四处,独留一颗淡黄色的花蕊。
桌子上的空余的位置,摆着他俩为数不多的几次旅游留影。桂芬走回书桌前,抬手抚摸镜框边缘。照片里的天安门广场前,老李挺直腰板意气风发,桂芬得站远了,蹲在地上,才能把他与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定格进同一画面。老李说过,在我们这儿,国家不是冷冰冰的概念,而是像你和我这样,千千万万个家庭。桂芬记起他们在寒风中哆哆嗦嗦等到黎明,当千万缕曙光照在红旗上的那一刻,老李悄悄拭去的泪花。他总是感叹,这样的体验一辈子只有一次吧,北京太远了。桂芬安慰他说等退休了再去看多少次都成。他们还约定以后要去很多地方,老李带起花镜摊开地图,认真做着攻略。但后来因为膝盖的病变,加上女儿的婚事,旅行计划一再耽搁,最后在老李那场大病后画上句点。
家里的账本记录着点点滴滴,一直都是老李在管。老李把两人的退休工资用黑笔记下,日常支出和储蓄用蓝笔记录。本子上流转着的数字,停在封城前的那天。清晨人们还在抱怨太阳的毒辣,工作的辛苦,物价的波动,到了晚上,城市便按下了暂停键。夏天的气氛迅速萎缩,很快陷落于一片荒芜。一段时间里,她守在电视机前,祈祷今日播报的数字会是零,这样她就能早点出门去看女儿,给女儿炒菜炖汤,可数据一天比一天可怕。社区工作人员开始连轴转,一人负责一整栋楼,送药、测温、报备、送货以及消杀,几天时间里就累倒三个,其余的人也是强撑着身体,分管了其他同志的任务。迫不得已,社区发起了志愿服务者的倡议。
桂芬明白,老李这次是要去的,因为这次就发生在身边,发生在眼前。她等老李挂掉打向社区的电话,走过去,说:“你一个老家伙去干吗?小区里那么多年轻人,哪能轮到你?”
老李拍着大腿,笑着说:“你之前不还嫌我退休没多久就开始发臭了吗,怎么现在又觉得我年纪大了?后生娃娃们上班上学多辛苦,现在好歹也算暑假了。这个时候不就靠着我们这些退休没多久又闲不住的老家伙吗?”
等老李披挂上防护服的那天,桂芬在心里轻轻问了句:你不怕吗?
其实那个时候,桂芬想的是,无论心中的色彩有多么鲜艳,信仰有多少分量,都改变不了血肉之躯的事实。她能觉察到他俩都在一点点变老,并越来越眷恋过去。她觉得老李不该这么拼,属于拼搏的日子,年轻时早就体验过了,现在应该放松神经过段自己的日子。这个年纪,疾病与意外不会留给人太多的侥幸。这不是对自私的辩解,而是作为妻子最普遍的想法。但是她没对老李坦白过。她怕的,是刺伤这个男人心中最温柔的位置。
(未完待续)
特邀编辑:董学仁
责任编辑:龚蓉梅
来源: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xiezuogongyuan.com/9794.html